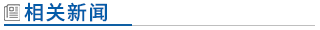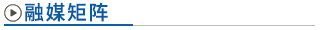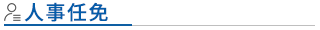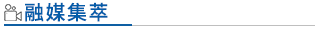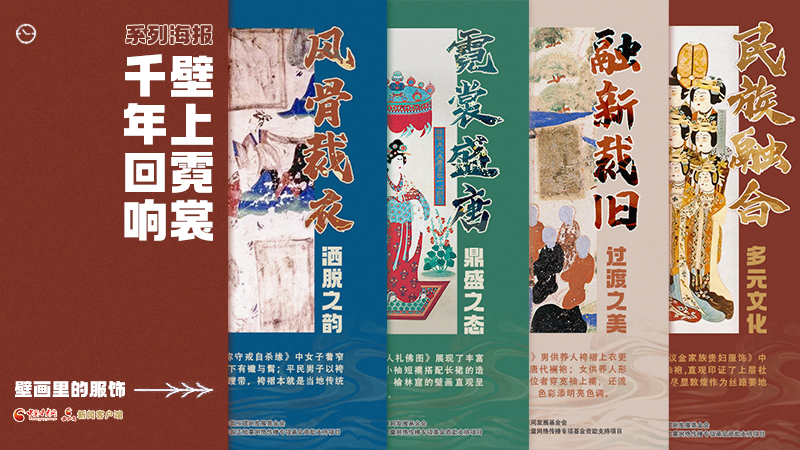李自新在創(chuàng)作仕女圖

500羅漢長(zhǎng)卷
七里河區(qū)八里鎮(zhèn)有一個(gè)剪紙世家,他們的傳承脈絡(luò),猶如一條堅(jiān)韌的絲線,串起了柳金花、李自新、李麟桐三代人的心血與熱愛,延續(xù)著剪紙藝術(shù)的燦爛火種。從母親柳金花老人的炕頭花樣,到兒子李自新的300米長(zhǎng)卷,再到女兒李麟桐的創(chuàng)新發(fā)展,剪紙對(duì)這個(gè)家庭而言,早已超越藝術(shù)的范疇,成為血脈中流淌的文化基因。
紙間天地:工作室的時(shí)光印記
在七里河區(qū)八里鎮(zhèn)后五泉村李自新工作室,首先映入眼簾的并非滿墻的剪紙,而是造型各異、靜立窗邊的根雕作品。直到轉(zhuǎn)身推開里間的門,一個(gè)用剪刀裁出的世界才豁然展開。桌上一幅幅剪紙作品整齊排列:全長(zhǎng)300米的《500羅漢》氣勢(shì)恢宏,70米長(zhǎng)的《水滸108將》栩栩如生,《敦煌壁畫》的莊嚴(yán)瑰麗與《紅樓夢(mèng)》的婉約靈動(dòng)交相輝映。而走進(jìn)李自新老人的家中,景象卻截然相反——房間里沒有直接陳列的絢麗作品,取而代之的是一摞摞用舊報(bào)紙仔細(xì)包裹、分類碼放的剪紙珍品。空氣中彌漫著宣紙的清潤(rùn)與舊報(bào)紙的陳香,層層紙頁之下,藏著的是李家三代人以剪刀為筆、宣紙為箋,剪出的家的味道。
工作臺(tái)前,李自新老人正伏案創(chuàng)作。他的工具攤滿桌面:大小不一、型號(hào)各異的剪刀不下二、三十把,刀刃在光線下閃著寒光;各種刻刀、鑿子,柄身已被磨得溫潤(rùn)。他正在創(chuàng)作的是《中國古代仕女圖》系列中的一幅,只見他手握小刀,全神貫注,刀刃在紙上游走,發(fā)出極細(xì)微的“沙沙”聲,精準(zhǔn)地剔除著不需要的部分,一個(gè)發(fā)髻盤起、衣袂飄飄的仕女形象正逐漸變得清晰、靈動(dòng)。
刀耕不輟:第二代傳承人的藝術(shù)之路
今年76歲的李自新,是非遺剪紙藝術(shù)的第二代傳承人,其藝術(shù)血脈源于他的母親——第一代傳承人柳金花女士。他自幼便在母親剪紙、繡荷包的指尖藝術(shù)中耳濡目染,對(duì)民間藝術(shù)產(chǎn)生了濃厚的興趣。及至年長(zhǎng),他的愛好愈發(fā)廣泛,不僅深研剪紙,更在泥塑、根雕、盆景、黃河奇石等諸多領(lǐng)域皆有所成,這些藝術(shù)形式彼此滋養(yǎng),豐富了他的審美與創(chuàng)作語言。在他眼里,剪紙的靈魂就是雕、刻、剪、鑿。
“我是從1989年開始學(xué)習(xí)剪紙創(chuàng)作的,”李自新回憶道,“最開始選的類型就是花鳥,因?yàn)橄鄬?duì)簡(jiǎn)單,是基礎(chǔ)。”然而,他很快就不滿足于此,將目光投向了更為宏大、復(fù)雜的題材。“后面開始剪羅漢、敦煌壁畫。那時(shí)候,心里就憋著一股勁兒,想要挑戰(zhàn)最難的傳統(tǒng)藝術(shù)精華。”
這份挑戰(zhàn),意味著長(zhǎng)達(dá)數(shù)十年的堅(jiān)持。“那時(shí)候,每天不管刮風(fēng)下雨、禮拜天、逢年過節(jié)都沒有間斷過。”他的話語平靜,卻透著一股強(qiáng)大的韌勁。最近,他的創(chuàng)作焦點(diǎn)轉(zhuǎn)向了中國古代仕女,試圖在柔美的線條中展現(xiàn)東方女性的神韻。
談到創(chuàng)作過程,他眼神中閃爍著匠人的嚴(yán)謹(jǐn)光芒:“剪一個(gè)好作品,首先要有一個(gè)構(gòu)思,然后再把它畫出來,再去動(dòng)剪刀、刻刀各種工具。” 在他這里,剪紙絕非簡(jiǎn)單的“剪花樣”,而是嚴(yán)謹(jǐn)?shù)乃囆g(shù)創(chuàng)作,是“胸有成竹”后的“運(yùn)剪如風(fēng)”。
李自新與母親柳金花、夫人王曉明組成的“藝術(shù)一家”,早在1992年蘭州市第一屆藝術(shù)節(jié)上,就以母親的傳統(tǒng)剪紙荷包、他的根雕、夫人的現(xiàn)代俏色剪紙聯(lián)袂參展,贏得了“藝術(shù)一家”和“一家巧藝自生春”的贊譽(yù)。斗轉(zhuǎn)星移,十六年后,李自新先生人老藝精,積累愈發(fā)豐厚。
薪火相傳:剪刀剪不斷家的情懷
“其實(shí)每一個(gè)人,在學(xué)習(xí)的過程當(dāng)中,都有一個(gè)引路人,我也是這樣的。”李麟桐是李自新的女兒,如今是剪紙非遺第三代傳承人。她的啟蒙源于2003年父親的一個(gè)突發(fā)奇想。“父親想做一些燈籠,需要大量的剪紙作品,于是號(hào)召全家動(dòng)手。”
“那個(gè)時(shí)候家里最大的話題,就是晚上總結(jié)誰的剪紙作品好,家里頭掀起了互相比拼的高潮。”她模仿著父親的語氣,“比如,今天妹妹剪了一個(gè)作品,父親馬上就說,‘哎呀,你看你妹妹剪的這個(gè)作品,人物和線條特別的細(xì),剪得也很好!’于是,明天我非得要剪一個(gè)比妹妹更好的作品。”這種家庭內(nèi)部的良性競(jìng)爭(zhēng),讓剪紙從一項(xiàng)技藝,變成了充滿樂趣的親情互動(dòng)。
然而,真正讓她意識(shí)到剪紙承載的重量,是在十年前母親去世之后。“我覺得家對(duì)每個(gè)人都有一個(gè)獨(dú)特的情懷,怎么樣把這個(gè)家的情懷永遠(yuǎn)地保留下來,一直刻在兄妹心中。”一次剪紙時(shí),她突然憶起童年:“小時(shí)候在蘭州過年,奶奶就在炕席底下拿出花樣教我們剪紙。那時(shí)候過年時(shí)窗戶要貼上花花綠綠的窗花,象征對(duì)來年美好的祝愿。”
“每逢想起這些,家的情懷油然而生。”這份頓悟,讓她堅(jiān)定了傳承的信念,“現(xiàn)在我也是兩個(gè)女兒的媽媽。奶奶和父親的手藝要繼承下來,以后讓我的孩子也要記住家的情懷。” 如今,她的小女兒也在課余時(shí)間跟著描摹畫稿,學(xué)習(xí)基礎(chǔ)。
以剪為橋:讓非遺的光芒越剪越亮
李麟桐明白剪紙創(chuàng)作的甘苦:“有時(shí)靈感來了,晚上舍不得睡覺,趕快將構(gòu)思的畫面記錄下來。”這種狀態(tài),她從父親身上早已見過——“父親以前,桌子旁邊就是床,有的時(shí)候半夜靈感來了,爬起來就開始剪紙。”
她闡釋著剪紙藝術(shù)的核心理念:“剪紙給我們這些手藝人提供的只有陰和陽兩種顏色。”如何用這兩種顏色表現(xiàn)大千世界,關(guān)鍵在于“線線相連”。“比如要剪一個(gè)人物,我們要保證讓他的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嘴,都是完整的。這就需要巧妙處理‘陰刻’和‘陽刻’的關(guān)系,才能既表現(xiàn)人物豐富的表情、眼神方向、手中物件,還有衣服的褶皺。”
李麟桐介紹,剪紙多用宣紙,因其不易掉色且兩面顏色一致。但宣紙中的草梗有時(shí)會(huì)帶偏刀鋒,因此力道掌控至關(guān)重要。“剛開始只能從對(duì)稱的基礎(chǔ)花樣開始,慢慢把手練巧,再擴(kuò)大畫面,加入人物、背景、風(fēng)景,融入自己的創(chuàng)作,才能形成自己的作品。”
她的作品既有繼承父親的《500羅漢》等宏大題材,也有《梅蘭竹菊》等雅致小品。“父親把花樣給我,我進(jìn)行再次創(chuàng)作,因?yàn)槲乙蚕氤剿?rdquo;她笑著說,有時(shí)會(huì)覺得父親作品中某些細(xì)微處還能再處理,便會(huì)融入自己的構(gòu)思,使作品呈現(xiàn)出不同的韻味。她最近正在創(chuàng)作《紅樓夢(mèng)》系列人物,已完成70多幅。
李麟桐對(duì)剪紙藝術(shù)的發(fā)展充滿了期待。她希望能夠繼續(xù)傳承和發(fā)揚(yáng)家族的剪紙技藝,讓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愛剪紙藝術(shù)。她計(jì)劃推動(dòng)剪紙教學(xué)活動(dòng)走進(jìn)學(xué)校、社區(qū),將剪紙的種子播撒在孩子們的心中。她還希望能夠與更多的藝術(shù)家和文化機(jī)構(gòu)合作,將剪紙藝術(shù)與現(xiàn)代科技、時(shí)尚設(shè)計(jì)等領(lǐng)域相結(jié)合,開發(fā)出更多具有創(chuàng)意和實(shí)用性的剪紙產(chǎn)品,讓剪紙藝術(shù)在新時(shí)代煥發(fā)出新的活力 。
記者 孫建榮 見習(xí)記者 包玉霞 文/圖

 西北角
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(wǎng)微信
中國甘肅網(wǎng)微信 微博甘肅
微博甘肅 學(xué)習(xí)強(qiáng)國
學(xué)習(xí)強(qiáng)國 今日頭條號(hào)
今日頭條號(hào)